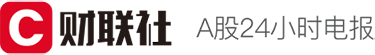或许能够这么说,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烈酒世界的两个佼佼者——苏格兰与法国一直在对峙,这一定是欧洲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烈酒冠军之争,但在过去这两个民族还曾是“老同盟”的盟友。
早在18世纪末,人们可能就预知了结果,并把一切赌注都压在了干邑上。干邑在英国、爱尔兰和欧洲大陆有一个成熟的市场,尽管在滑铁卢发生了一些小争执,但法国干邑对英国的进口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期。虽然,当时征收的高额关税可能会阻碍干邑的发展,但狡猾的走私者总能找到办法。
与此同时,大多数苏格兰威士忌都是通过非法蒸馏而生产出来的,当地人大多喜欢饮用未经陈年的新酒。这往往都是现成的糙酒,可以说,是没有机会赢得烈酒世界的冠军的。然而,这却是一个从零到有的崛起过程。1822年,汉诺威王室的乔治四世访问爱丁堡期间,喝了大量的格兰威特威士忌。之后,苏格兰农民非法酿造出的威士忌便出名了,至少在斯佩塞地区,产量持上升状态。
然而,几番轮回后(大约在19世纪60年代),当一项允许今天的著名品牌建立的法案颁布后,干邑开始变得强大起来。要知道,在之前,酒瓶上写的都是进口该酒的商人的名字,而不是生产商的名字。不久之后,英国降低了干邑的关税,干邑于海峡两岸的销量在15年内增长三倍。而此时,苏格兰威士忌的情况看上去不是太好,但比赛还没有结束。
19世纪末,葡萄根瘤蚜虫穿越大西洋,消灭了欧洲大部分的葡萄园,这令法国人(以及拥有较多葡萄树的人)感到震惊。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天平便由葡萄制作的饮品向谷物制作的饮品倾斜,威士忌成了苏格兰的国民饮品,受到了来自商人、贫民、专业人士、皇室成员等不同群体的青睐。
干邑的发展岌岌可危。当苏格兰人在为理想的数据沾沾自喜时,1898年的帕蒂森危机却让他们摔得惨烈。市场萎缩、生产过剩,整个苏格兰威士忌行业因此陷入困境。两次世界大战和美国的禁酒令让法国与苏格兰雪上加霜,直到20世纪中叶,他们才重新站了起来。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为争夺有眼光、有形象意识的酒类消费者的战斗一直在继续,无数次的进攻和撤退导致了双方的胜利和失败。这些攻防战都是在公开市场上进行的,在这里采取明智的营销策略或在当地扩大分销,都可以获利。
值得注意的是,双方并不总是公平竞争。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重大事件中,苏格兰威士忌行业在短短几年内就 “颠覆”了台湾市场对干邑的偏爱,部分原因是通过宣传威士忌是法国干邑的“健康”替代品,据称法国烈酒中含有大量的液体糖,当然,苏格兰威士忌行业根本不会想到这一点。
要知道,这一切都发生在《1990年苏格兰威士忌法令》颁布后不久,该法令禁止苏格兰威士忌中的所有添加剂(包括迄今为止被广泛使用的Paxarette糖浆),但无味焦糖色素除外。因此,法国干邑的液体糖用量也受到了其反对者的抨击。
撇开古老的历史不谈,从这次苏格兰威士忌和干邑平行的命运旅程中应该了解到的是,这两种产品在历史上一直是市场上的竞争对手。然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威士忌制造商正在利用干邑的特点来推广他们的产品,无论是利用法国橡木桶、曾经装过干邑的木桶、风土语言,还是能让人联想到法国“我行我素”的风格特性。如今已有迹象表明,法国和苏格兰的酿酒师们并不仅仅单纯地想要超越对方,他们更想越过围栏,着眼烈酒市场上,看看能从对方身上直接学到什么。
首先,近来珍稀的高年份苏格兰威士忌的包装设计变得越来越高档,这足以证明法国人对苏格兰酿酒师的启发。过去,即使是最稀有、最珍贵的威士忌,也基本都装在简约的瓶子里,不过一些稍微亮眼一些的麦芽威士忌和调和威士忌可能会被贴上一个花哨的标签。人们总是对来自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超奢华酒瓶抱有期待,但如今,当谈到奢华、高端的设计、以及复杂的手工吹制水晶酒瓶时,很难决定哪一类酒瓶更胜一筹。
更多跨越品类的灵感上的证据是使用干邑旧桶进行熟成。Glenfarclas、Glenmorangie、Arran、Douglas Laing、Hazelburn、Kilchoman、Balvenie等威士忌都曾使用过特殊的法国干邑桶。最近,著名的干邑桶威士忌Chivas XV(其名称是对干邑“XO”分级的微妙敬意)和格兰威特的Captain s Reserve都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它们的干邑桶熟成的特性。另一款由同样著名的斯佩塞酒厂生产的干邑桶陈年威士忌“hero product”目前还处于保密状态,预计2021年上市(由于疫情影响,推迟了一年),并将借鉴法国最杰出的酒的味道和故事。
同时,一些具有创新精神的法国生产商也采用了桶陈的技术来研发特别的酒款。这种做法在苏格兰很常见,但在干邑的领域里,由于规定十分严格,所以这种品类几乎没人听说过。例如,2016年,马爹利出现了一款颇具争议的版本,它是在波本桶中熟成的,为了规避法国国家干邑酒行业管理局(BNIC)的规定。它只能被标为“eau de vie de vin”而非干邑。2017年年底,Courvoisier的雪莉桶珍藏大师系列上架,而最大的独立干邑公司Camus则进一步提升了干邑的档次,推出了他们所说的第一款波特桶干邑。
在当代看来这是很特别的,但Camus认为,早在20世纪中叶,干邑生产规则收紧之前,波特桶就有出现过。它用先前盛放茶色波特酒的木材制成,紧接着在另一种原先盛放Monbazillac甜酒的容器中二次熟成。这些酒的发行触犯了当时BNIC的规定,因为从技术上讲,干邑应该是在一个原先盛放红酒或基于红酒的烈酒的木桶中熟成。然而,据报道,这个漏洞现在已经被堵住了,所以目前看来,这种跨品类的途径无疑是条单行道了,现在已不太可能在短期内看到干邑桶苏格兰威士忌。
然而,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关联之外,人们还想知道是否还有更值得分享的高深思想与价值观。尽管许多苏格兰威士忌品牌已从法国人那里学到了一些关于奢侈品营销的方法,但事实上苏格兰威士忌还有更多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不仅仅在于华丽的包装和酒桶的选用方面。
人们也在探讨酒厂的风土、 野生酵母、和本土大麦的发展,这说明很多苏格兰威士忌公司都在倾听欧洲近邻的意见。Camus这个家族企业便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生产商之一,由于过桶的路径行不通,且还需遵守BNIC的规定,Camus开始寻求更多创新的机会,希望他们的品类可以更加丰富。
Camus再也不能使用特殊的酒桶了,而且干邑的种植区域或“Crus”和葡萄品种也已定型,于是Camus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可以自由改变的因素:熟成环境。这从Île de Ré系列便开始了,该酒款完全由La Rochelle海岸附近古朴岛屿上种植的葡萄酿造而成。悬崖边上的酒窖混合着一种香水的气息,悬崖峭壁上有许多Camus酒桶。潮湿的环境、狂风的吹拂和巨大的温度波动,在这种环境中熟成的干邑,特性与在内陆中熟成的干邑截然不同。
在这一成功的激励下,该公司最新推出Camus Caribbean Expedition,将该公司的酒装上高大的轮船,进行海上旅行,前往巴巴多斯,重现历史上的跨大西洋贸易路线,在那里卸下酒桶,放在Four Square朗姆酒厂的仓库里。
在Four Square酿酒大师Richard Seale的注视下,在这种热带气候中经历了一年的熟成期后,这些酒桶再次被装上高大的轮船并返回法国。暴露于高湿度的浓雾、高温天气以及湍流中,这次远征创造了一款独特的干邑,它在旅途中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是在本土无法复制的。
虽然SWA的规定会阻止类似的实验发生在苏格兰单一麦芽威士忌的世界里,但地处悬崖边的酒窖也呈现出一种有趣的想法。随着对风土等概念的重新关注,苏格兰威士忌的呈现方式定会占有一席之地,这些威士忌完全是在超本地化地或非传统环境中熟成的。众所周知,苏格兰的大多数酿酒商都是在中央带式仓储中熟成威士忌的,同时利用酒厂荒僻的地理位置、独特的当地气候和浪漫的传统仓储进行交易。
一些勇敢的酿酒师不再混淆视听,而是去尝试不同地区熟成的酒。甚至对于更有创新精神的品牌来说,他们在苏格兰其他地区熟成自己的威士忌,因为,其气候与自身酒厂附近的气候截然不同。另外,与其遮遮掩掩,不如尝试将熟成地点作为一个值得宣扬的特性,为在不同条件下熟成的酒提供一个比较与参照。
事实上,一些新兴的酒厂正在研究浮式仓储,这表明一些酒厂显然也看到了熟成环境所隐藏的潜力,这与木桶在出口过程中在海上享受时光一样。这些途径是否会催生下一代的苏格兰威士忌,谁能说呢?可以肯定的是,苏格兰与干邑之间的联系或许比一些酒桶更值得学习。
经公众号“WM世界威士忌资讯”(ID:WhiskyMagazine_China)授权转载。原文及标题略有改动。
图片来源于《威士忌杂志》,版权归原作者所有。